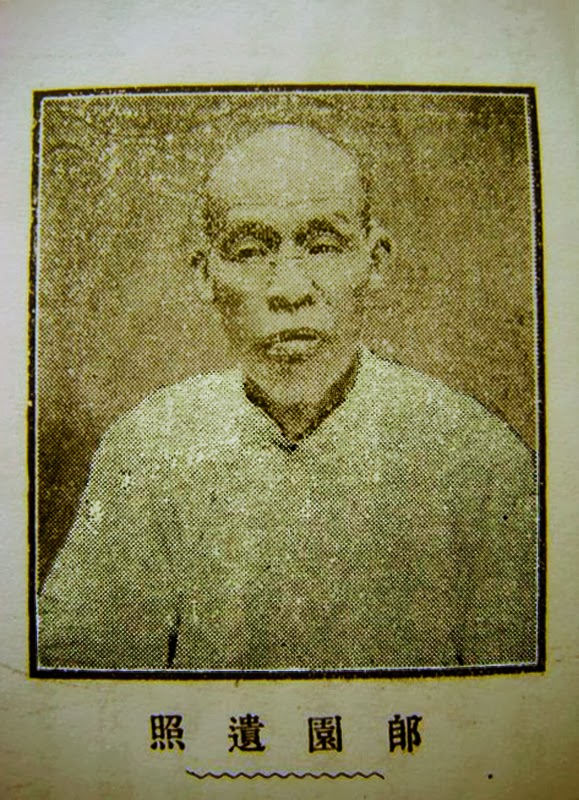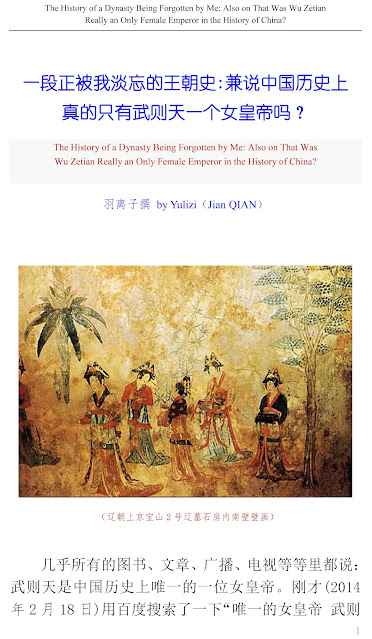Something Are Not Really so Contradictory
– about Ye Dehui's Death
一些事其实不那么矛盾:看叶德辉之死
羽离子撰 by Yulizi
对于究竟是谁抓杀了他的,这些年来则更有新说,例如虽年轻但研究已颇深的谭伯牛君在2007年3月的《南方周末》上发表《叶德辉之死真相:毛泽东曾说杀他不妥当》一文而称“胡适犯了两个不能‘小心求证’的错误,第一,杀叶德辉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省党部领导下的特别法庭;……”
(郋园是叶德辉的号)
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文献学家沈津先生于2008年写《也说叶德辉之死》一文,谓:“我就知道了写葉德輝死因的是譚伯牛先生,文章写得很好,有理、有据,分析得头头是道。”
如一些史家所知所引,叶德辉长子叶启倬(字尚农)致其父之友日人松崎柔甫的信中有记:“今将先父遇难被害各情节,涕泣陈之。先父于夏历三月初七日晚六时,被农工界在家捕去,送押长沙县署内。当即遍恳有力各要人,出为救援,均归无效。初十日,由长沙县转送特别法庭,于下午三时提讯一次;所犯刑律:帝制嫌疑。四时,送往浏阳门外识字岭枪决。身受两枪,一中头部,一中心部;遂遭惨死。”信中提到的长沙县署和特别法庭分别是武汉国民政府统治的湖南省的一常设而一临时的下属机构。
实情到底如何?我做了些查究;认识到的情况如下。
抓捕先前曾组织筹安会湖南分会来赞划复辟君主制,如今又遭农民痛恨的长沙地主叶德辉的是实际成为了乡村政权的农民协会,处死他的是由国民党、农民协会、湖南省政府、军队所派的五名成员联合组成的代表“工农界”的临时的特别法庭。其五名成员中,谢觉斋(即谢觉哉)、戴述人、易礼容三人即均是担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常委和监察委员的中共党员。谢觉斋还任该党部工人部部长, 易礼容则兼管湖南省农民协会。另外两名是湖南省高等检察厅厅长吴鸿骞和湖南省军的军法官冯天柱;这两人都属国民党左派。
特别法庭又何以由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授权成立?那是因为彼时在南方军政势力覆盖的区域里是“党国”一体,党务指导政务,党之令即政之策。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叶德辉早先曾为了救国民党员而差点丢了性命。1913年,国民党发动了旨在推翻袁世凯专制统治的“二次革命”,汤芗铭奉袁世凯令而带了几艘海军舰艇来江西、湖南镇压革命。汤芗铭十分卖力,进兵湖南逼走了响应革命的省都督谭延闿后,被北洋政府任为省都督。汤为了获得袁世凯的信任,在上任之后大肆捕杀国民党员和反袁人士;被杀者中仅有名姓可查的就达两万多人;一时阴风血雨,恐怖非常。汤芗铭还有其它恶政。向来逆潮流而动的叶德辉不顾自家性命,于次年写信给杨度斥陈汤芗铭的作恶行径,请杨度代告总统袁世凯以束办。哪知《亚细亚报》的主编不知从何渠道看到此信,认为是个卖点而将之登在了报上。年届五十的叶德辉遂被盛怒之下的汤芗铭抓去。易培基闻知后急请黎元洪营救;徐世昌、徐树铮、李燮和、叶恭绰等等也在稍后纷电湖南,连叶德辉的死对头熊希龄和梁启超也发声要保他一命。众人终至于赶在汤芗铭下令正法叶德辉前把他的命救了下来。谭伯牛的文中也再述了这一旧事。
而1927年4月上旬,叶德辉被农民协会捕去时,统领湖南省的武汉政府尚未国共分裂,汪精卫等为对抗蒋介石等而正在继续包容中共。中共党员仍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而发挥作用;中共和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农会、农民自卫队、工会、工人纠察队等等也仍然多奉照或借用国民政府或国民党的名义行事。在后来湖南的马日事变和武汉的七一五政变相继发生后,中共和国民党左派才被迫脱离已被国民党右派控制的武汉政府和彻底脱离已右转的国民党系统而开始由中共领导了在全国多处城乡的武装暴动以建立独立的军事力量。
简要地温习了上述历史,就可以知道,谭伯牛等的论述似乎与叶德辉是由革命团体等大会所决杀的旧说看似相矛盾,其实并不矛盾了。
记述叶德辉之死的其它情节其实也不那么矛盾。农协会员们冲进大院来抓叶德辉时,正在洗脚的他立刻躲进另一个院落中的倒扣的水缸里——过去人家是常常把不用的水缸倒扣起来的;所以,说他是洗脚时被抓和是在水缸里被抓的两种传说都对。他先是被枪毙的,后来有人再戳上几梭镖,就像皇清时把人勒死了有时还要在尸身上插几刀一样。……
叶德辉一生嗜书如命,是大藏书家又精于版本之学。今人研究古典文献学,可能会触及此人;而围绕他的死又众说纷纭,所以作此小文。如果读者对我的一家之言仍表狐疑,那也不要紧;因为或许该读者还真地能把旧事考查梳理得更为实在与通顺。
(《羽离子文汇》,Y编;2014年版,第4-6页)